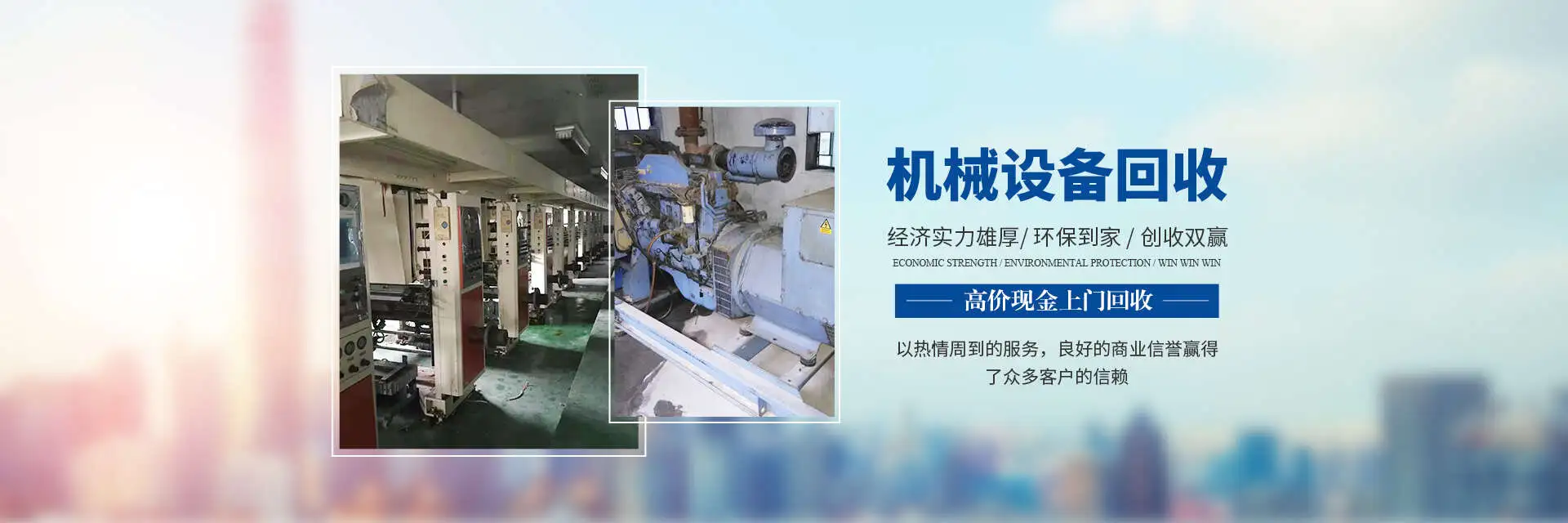塑料垃圾的跨国之战:大量未经处理进入中国
一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,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,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从最初的7.4亿美元飙升到115.4亿美元。
庞大的进口垃圾,在中国是如何完成资源回收利用的?期间产生的污染问题如何解决?
一部26分钟的纪录片——《塑料王国》,揭开了关于进口垃圾处理的残酷真相,却在中国再生资源行业内外,掀起一场争论。
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,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垃圾进口国。
一个概念需要厘清——经过分拣和清洗的塑料垃圾,属于国家允许进口的可再生资源。
另一个概念同样需要厘清——从生活垃圾中去分拣和清洗塑料垃圾,不仅涉及必要的分拣技术,更需要足够的处理伴生污染的能力。
问题随之而来。
所有进入中国的塑料垃圾,都已经完成了必要的分拣和清洗了吗?如果没有,这就意味着这些分拣和清洗的程序都要在中国进行。那么,我们对伴生污染的处理能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平?现实中的塑料垃圾处理真能严格执行污染处理的所有要求吗?
经过28个月的跟踪拍摄,中国塑料垃圾处理的真实场景,触目惊心地显示在纪录片导演王久良的作品之中,尽管他选用一个不无中性色彩的名字——《塑料王国》。
在冷峻而不加掩饰的镜头下,大量未经处理的塑料垃圾进入中国,散布在从北到南的30多个大小乡镇,最终在一个又一个小作坊里,由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工人用手完成了粗糙的分拣。接下来,清洗塑料垃圾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流,无法再生利用的废弃垃圾在农田边焚烧,黑色的浓烟充满着刺鼻的气味。这些村庄里,地下水已经无法饮用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罹患癌症。
这是一个关于垃圾的残酷真相,更是一个关于贫穷、人性、逐利、价值观的故事。
塑料引爆话题
当垃圾处理成为一门生意,抢夺垃圾的战争就已经打响。
通常的观点认为,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。不能否认,这个观点成为垃圾产业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理论支撑,甚至有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共识。
但是,在与垃圾打过7年交道后,王久良坚持认为,“垃圾等于资源”不过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状态,因为它完全忽略了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巨大污染。“至少从目前看,混乱的处理过程和低下的处理能力,使得中国的垃圾处理仍然是一个负增值的产业。”
就在北京奥运会隆重举办之际,王久良开始骑着自己的越野摩托,像猎犬一样在北京城周边游荡,遍寻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垃圾场,再把代表每一个垃圾场位置的黄色图钉密密麻麻钉在北京地图上,用最直观的图景震撼了所有看到这幅地图的人。
这次为期3年的遍寻垃圾场行动后,王久良推出均以《垃圾围城》为题的摄影作品和纪录片,这4个字也一度成为环境保护浪潮的热门词汇,甚至引发中央领导关注批示。随后,北京市宣布投资100亿元,用5到7年时间完成对周边近千个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治理,并建设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厂。
经此一“役”,更主要的是建立在大量实地调研和影像资料的基础上,王久良对于垃圾问题的意见表达,已经显示出民间独立调查性质的权威性。
即将进入2015年的时候,王久良再度发声,用一部暌违3年的纪录片新作《塑料王国》,撕下了一个以再生资源回收、循环经济为名的产业的面纱,暴露出最为不堪的一面。
来自中国海关的官方统计,2013年,我国进口废旧塑料垃圾总量为800多万吨。王久良所记录的,正是这些垃圾在中国从南到北30多个乡镇村庄最真实的初级加工场景。
《塑料王国》第一次面向媒体的放映地点,选在北京东二环边的银河SOHO大楼。这座宣称拥有最好空气净化系统的建筑物,远远望去充满着时尚的未来感。
但是,至少在放映的这一天,银河SOHO的未来感被笼罩京城的雾霾粉碎肢解。当天,空气中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,成为《塑料王国》所要表达主题的又一个注脚。
源源不断的集装箱货车,拉着满满的垃圾进入村庄。留守农村的妇女和老人,还有那些来自更贫穷地区的打工青年,在乱糟糟的作坊里用手分拣着塑料垃圾。这些垃圾的“原产地”,多是美国、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韩国和澳大利亚。在镜头里,很多生活塑料垃圾里面掺杂着不明化学粉剂,灼伤了翻检者的双手。甚至还有一个在垃圾堆旁玩耍的孩子,拿起一个还残留着不明液体的针管,毫无戒备地直接放进嘴里玩耍。
这场景在银幕上出现时,观众发出抑制不住的惊呼。那些充斥着肮脏垃圾、浓烟、污染水的画面,那些依赖垃圾处理维系生存者的麻木与无奈,与重重笼罩都市的雾霾天气遥相呼应,让人产生一种几近环境末日的关联想象。
“我们这样落后的垃圾处理能力,为什么还要进口洋垃圾?”几乎每一位看过《塑料王国》的人,都会不解愤懑地提出这样的问题。
无疑,王久良又扔下了一颗炸弹。
巨响过后,中国乡村垃圾处理的残酷真相浮出水面。
战绩与现实
一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,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,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,从最初的7.4亿美元飙升到115.4亿美元。
疑问就此产生——中国为什么进口这么多垃圾?
王久良的回答可以概括为四个字——“利益驱动”。
“过去,一些国家的生活垃圾是需要花钱向外转移的。后来,这种垃圾慢慢有了市场,不用付钱也可以转移出去。现在,一切都颠倒了,生活垃圾竟然成为可以出售的商品。”在纪录片《塑料王国》放映前,王久良告诉记者,正是中国的进口抬高了世界垃圾的价格。
不过,王久良的观点一经曝光,便立刻招致资源再生行业相关者的强烈反对。27岁的再生资源网站编辑于泽甚至私信王久良,直接表达反对的态度。
2015年1月2日,于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断然表示:“没有人否认存在过进口洋垃圾的问题,但在绿篱行动以后,那种情况已经几乎不可能发生。”
于泽所说的绿篱行动,是国家海关总署于2013年2月启动的一次为期10个月的专项行动,旨在加强固体废物监管、严打洋垃圾走私行为。
“过去,进口的集装箱是抽检。在绿篱行动中,几乎箱箱检查,并且实行最严格的掏检。”于泽拿出一份新闻报道,上面列举了各地海关的行动成果,其中,仅在黄埔海关、烟台海关、宁波海关、黄岛海关、威海海关、青岛海关、梧州海关、佛山海关和石家庄海关,便共计查办涉案废塑料3万多吨。
“王久良的拍摄期,一定是在绿篱行动之前。”走访过很多大型正规再生资源企业的于泽,对国家的专项打击行动效果深信不疑。
“你信吗?”听完记者转述的于泽观点,王久良这样反问。“确实有段时间,拉垃圾的车少了。但有的老板直白地告诉我说,别管他们的货滞留多长时间,最后总有办法通关提走。”
事实上,究竟如何定义洋垃圾与合格废旧塑料原料,本身就界限模糊。
在于泽看来,国家的规定很明确。以废旧矿泉水瓶(PET)为例,需要在垃圾出口国完成清洗和拆解后,才能作为再生资源原料被进口到中国。
然而,现实显然并不是这样。
2011年,王久良访问美国加州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。参观结束后,美方人员不经意间指着正要开走的集装箱货车说:“你看,那是要运往你们中国的。”
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的垃圾,都是生活垃圾。经过人工初步分拣,生活塑料垃圾被分离出来。正是这些美国人不愿花钱费力处理的垃圾,被中国的商人买走。
这个不经意间的发现,让王久良产生疑问——令美国人头疼的垃圾运到中国后,到底又会如何处理?
经过1年的调研,王久良决意再拍摄一部纪录片,追踪曾经困扰自己的事实真相。
2012年5月31日,《塑料王国》正式开机。整个拍摄持续了28个月,直到2014年9月结束。
“最初3个月,几乎处于被驱赶的状态,进入不了实质性的拍摄。这样算来,大部分的拍摄素材,正好是绿篱行动期间。”王久良直言,“我不用看数据,也不用听有过什么行动,我亲眼看到并拍摄下来的,足以说明一切。”
放错位置的资源?
毫无疑问,王久良和他的《塑料王国》,似乎触动了整个再生资源行业的“奶酪”。
于泽的质疑只是开始,更多的反击接踵而至。
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周开庆先生发表的文章中,重点援引了巴塞尔公约中的观点,“塑料被认为是无毒的”,“使用塑料再生料不仅仅是成本考虑,而是发展和责任考虑”。
与此同时,一些颇具规模的正规厂家处理塑料垃圾的过程,也被用来证明《塑料王国》揭示的原始和混乱仅为个案。
对此,王久良直接反驳——在进口塑料垃圾处理的问题上,不要把利润和社会责任混为一谈。如果为的是利润,那么由此产生并在未来逐渐显现的环境污染,为什么没有让从垃圾中掠取利润者“买单”?如果是为了社会责任,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塑料垃圾进行处理,到底履行的是哪家的社会责任?
在王久良看来,一切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,都是负增值产业。如果环保型回收1吨废旧生活塑料能够产生100元经济效益,需要付出的成本,至少也要101元。否则,便无法解释在被世界公认垃圾分拣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,为什么要对企业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补贴,更解释不通为什么《塑料王国》里依然会出现日本垃圾。
事实上,一些塑料垃圾处理企业一直在吁请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。他们在例证企业深陷经营困境时的说法,客观上暴露出环境污染问题的严峻。
“塑料作为可再生资源,要回收是一定的。但是,如果没有国家足够的政策支持,企业不好做的。”从事废旧塑料回收5年的安伟(化名)说。
这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从业者,来自国内某废塑料回收集中县。两年前,这个县对散落在村子里的小作坊式废塑料分拣、造粒产业,进行了“壮士断腕,涅槃重生”式的自我革命。公开的报道中,县政府高度重视环保问题,淘汰小作坊,引导成规模企业进入工业园区,目的只有一个——建立环境友好型的再生资源回收产业。
安伟毫不讳言政府对入园企业提供了多项支持,也承认园区经营者在租金上给予了相当优惠。“就拿处理废旧塑料产生的污水来说,处理成本至少在每吨10元以上。现在,包括水费和处理费用在内,每吨污水只向企业收取6元。”但是,即便是这些已经大大压缩的污水处理成本,依然是企业不堪其重的的负担。
其实,在污水处理这个环节之外,最终无法回收的垃圾如何处置,依然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大难题。依据王久良的调查,1吨塑料垃圾的回收率,即便在运气好的时候最多也只有85%,这就意味着至少要有150公斤废弃物毫无任何用处。
对于这些纯粹的垃圾,最普遍的做法依然是填埋或者焚烧。在王久良拍摄的画面中,很多垃圾就在田间露天燃烧,黑色烟尘弥漫。
“理论上,焚烧可以用来发电,但又是一笔巨大的投资,谁投?”安伟说。
填埋呢?科学研究已经证明,垃圾填埋对土地和地下水的污染破坏,影响时间长达上百年。
无论如何,王久良和他的《塑料王国》已经搅动了一个行业。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一切判断和论断,都来自长达3年的调查。“有多少园区污水厂根本就不运行?说是统一处理,可管道都没铺通,这些我都拍到了呀。”
可惜,诸多专业人士似乎看不到这些。周开庆在自己的文章最后,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:一家企业有问题,少数人有问题,不能推而广之。随着社会对中国再生塑料产业的认知和了解,一些片面的新闻报道已经很难对行业健康发展形成多大影响。
周开庆这样说:“我们坦然处之吧。”
然而,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处之吗?
房间里的大象
行业内外的争论还在继续。
但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,王久良作品中呈现的产业最前端从业者们的纠结、贫困、损害与被损害、麻木,才是戳中人们内心痛点的元素。
“垃圾(这)东西,又不是新的,没有味?什么味都有!”画面中,一位分拣垃圾的妇女这样说。
在《塑料王国》中,围绕着通过回收废旧塑料来挣钱究竟值不值,分拣垃圾的工人们有过这样一次讨论——
“可熏得慌了,熏有什么办法。”
“其实俺也不愿意干,这东西又脏又有污染,俺自己也知道,对俺自己也不好,但是俺为了生存,没办法。”
“空气空气不好,水水不好。什么好?说句开玩笑的话,就是钱好。”
……
王久良告诉记者,片子中出镜的女分拣工干了20多年,自从有了这个产业开始就干,到现在一个月收入七八百元。而她的手,每一块关节都是变形的。另一个老太太捡到一个瓶子,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液体,只是想回收这个瓶子。结果在倒掉液体的时候,她的一个指关节全被烧焦。“瓶子里的液体是氢氟酸,一种强酸。”
王久良到田间拍摄,问当地人这些垃圾对庄稼有没有影响,回答竟是“没污染,咱实事求是”。结果镜头一转,村庄的环境变得糟糕。干涸的池塘,已经多年不见鱼虾。处理废旧塑料产生的黑色污水,直接排入河流。甚至连地下水都无法安全饮用,村民需要购买山泉水喝。“一个月十五六元吧。”老太太算计着每个月买水的费用,售卖山泉水的小贩送水的步子匆忙。
村头,一位干废旧塑料回收的老板的老父亲说着,这年头,怎么年轻人都得癌?
另一个男人,反问王久良,“你要问还有谁没得癌?”
即便如此,每个人都在维护着这个产业。
产业链上,最低端却最必要的一环上,以生存的名义忍受脏臭乃至环境被破坏的人们,对理想生活的大胆奢望,其实极其卑微。
一个年轻的小老板,最大的理想就是买辆车。终于,在一个冬天,小老板实现了这个理想,兴奋地在自己新买的二手车里坐了半晚。
“人在车里产生的热气让挡风玻璃盖了一层白雾,从一个角看进去,那老板高兴的脸,当时那感觉,真是……哎……”王久良没办法忘记这一幕,那是以生存为代价换取的梦想实现,从他的价值观看来,个中滋味,难以评说。
一家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家庭,由于贫穷,年轻的父母亲带着孩子全家打工在一家分拣作坊。家里的女孩依姐(音)早已成为分拣塑料的熟练工。她最小的妹妹,出生在这个堆满了垃圾的院落外面。11岁的依姐渴望上学,父亲却一拖再拖,理由都是“没钱”。依姐最喜欢在老板家里玩电脑,在一次争吵后,两家人关系紧张,女孩就从垃圾堆里捡出花花绿绿的纸板,在桌子上做出了电脑的模样,自己打字玩。
垃圾,就是依姐这样的孩子全部的世界。他们在垃圾里成长,从垃圾中获得玩具,甚至从垃圾中学习。而垃圾,能够给他们的,也仅此而已。
“我真的无法喜欢上他们,除了那些孩子。”王久良并不讳言自己的情绪,他与他的被拍摄者们相处时间按年计算,他理解他们的无奈、挣扎和选择,但在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让他没办法从情感上喜欢上他们。
人们知道垃圾的危害,但没人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什么。正在野外倾倒塑料垃圾的人对着镜头说,为什么不查查谁让这些洋垃圾进到中国?
这个存在于30多个乡镇的废旧塑料回收产业伴生的污染问题,似乎没人愿意来管。垃圾,像房间里的大象,切实地影响着那么多的乡村和人们的健康,而所有人选择视而不见,以生存的名义。
选择不看的,还有那些垃圾输出国。
塑料垃圾从世界各国而来,在中国获得重生,被制造成玩具或者其他产品,又重新回到美国、德国乃至全世界的生活中。没人在意,垃圾如何重生?又留下了什么。
理想主义者的坚持
2014年的最后一天,王久良踏上赴美航班。他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,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。他筹划着要在纽约、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播放《塑料王国》,让美国民众了解自己产生的垃圾,最终给大洋彼岸的中国人带来了怎样的伤害。
正是在伯克利,王久良发现了中国这个“塑料王国”。那位出现在纪录片中的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负责人丹尼尔,在看过王久良在中国拍摄的部分素材后回应说:“现在我们看到了,我认为大家应该看到这些。”
王久良意识到,美国民众关于垃圾链产业中的道德伦理选择,可能会成为影响垃圾输出行为改变的力量。
看过《塑料王国》的很多观众意识到,垃圾并不会自己消失。当中国的大门关上了,这些垃圾还会流向地球上其它国家。“你们媒体在国内使劲,我在国外使劲,大家做各自擅长的。”无论如何,王久良下定了决心,“即使是冰山,也要撬动它”。
或许,很多人都误解了王久良。
2008年,王久良发现了垃圾,从此,垃圾也黏上了他。但是,他的思考显然并不止于如何处理垃圾以及垃圾的世界战争。从始至终,他的目标是希望提出一个更为终极的命题——消费主义时代里,人究竟拥有多少算够?
几年前,记者初次采访王久良,他用着一部老式的诺基亚黑白屏手机。今年,记者再次采访王久良时,惊讶地发现,在这个全民触屏智能手机的时代,他依然固执地使用着那部落伍了好几代的手机。
王久良不过度消费,他将自己的生活需求维持在最基本的层面。与垃圾打了6年交道,电脑里全是垃圾的素材,超市里那些花花绿绿琳琅满目的包装,在他眼里条件反射式地瞬间变成它们被使用后成为垃圾的样子。
“我很想做一个展览,就叫《超级市场》,货架上摆满的不是新商品,而是摆满喝完牛奶的空盒子,吃完冰淇淋的塑料桶什么的,让垃圾填满货架。”王久良希望,人们能够从垃圾问题上,检视自己的消费,而不仅仅只是抱怨政府做得多么不够,环境如何变得糟糕。
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,所有行业都在挖空心思如何让人们从兜里掏钱出来,王久良却试图让这浮华喧闹的消费快车跑慢一点。这多少有点唐·吉诃德的意味。
小时候,妈妈带着王久良算命。“那先生说我,一生‘骑着墙头当马匹,拿着秫秸当杆枪’。”现在,相机和摄像机就是王久良的“武器”。他唯一能够仰赖的东西,与算命先生所言的“墙头”和“秫秸”无异。在这位38岁独立纪录片导演内心,始终有着最为清晰且理智的坚持。“我能改变世界的很有限,但能改变多少是多少吧。”
王久良没有想到,自己从《垃圾围城》开始,竟然与垃圾黏在一起整整7年。
围绕着垃圾的拍摄计划,并未完成。看上去,他与垃圾还要继续黏下去。
庞大的进口垃圾,在中国是如何完成资源回收利用的?期间产生的污染问题如何解决?
一部26分钟的纪录片——《塑料王国》,揭开了关于进口垃圾处理的残酷真相,却在中国再生资源行业内外,掀起一场争论。
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,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垃圾进口国。
一个概念需要厘清——经过分拣和清洗的塑料垃圾,属于国家允许进口的可再生资源。
另一个概念同样需要厘清——从生活垃圾中去分拣和清洗塑料垃圾,不仅涉及必要的分拣技术,更需要足够的处理伴生污染的能力。
问题随之而来。
所有进入中国的塑料垃圾,都已经完成了必要的分拣和清洗了吗?如果没有,这就意味着这些分拣和清洗的程序都要在中国进行。那么,我们对伴生污染的处理能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平?现实中的塑料垃圾处理真能严格执行污染处理的所有要求吗?
经过28个月的跟踪拍摄,中国塑料垃圾处理的真实场景,触目惊心地显示在纪录片导演王久良的作品之中,尽管他选用一个不无中性色彩的名字——《塑料王国》。
在冷峻而不加掩饰的镜头下,大量未经处理的塑料垃圾进入中国,散布在从北到南的30多个大小乡镇,最终在一个又一个小作坊里,由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工人用手完成了粗糙的分拣。接下来,清洗塑料垃圾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流,无法再生利用的废弃垃圾在农田边焚烧,黑色的浓烟充满着刺鼻的气味。这些村庄里,地下水已经无法饮用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罹患癌症。
这是一个关于垃圾的残酷真相,更是一个关于贫穷、人性、逐利、价值观的故事。
塑料引爆话题
当垃圾处理成为一门生意,抢夺垃圾的战争就已经打响。
通常的观点认为,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。不能否认,这个观点成为垃圾产业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理论支撑,甚至有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共识。
但是,在与垃圾打过7年交道后,王久良坚持认为,“垃圾等于资源”不过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状态,因为它完全忽略了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巨大污染。“至少从目前看,混乱的处理过程和低下的处理能力,使得中国的垃圾处理仍然是一个负增值的产业。”
就在北京奥运会隆重举办之际,王久良开始骑着自己的越野摩托,像猎犬一样在北京城周边游荡,遍寻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垃圾场,再把代表每一个垃圾场位置的黄色图钉密密麻麻钉在北京地图上,用最直观的图景震撼了所有看到这幅地图的人。
这次为期3年的遍寻垃圾场行动后,王久良推出均以《垃圾围城》为题的摄影作品和纪录片,这4个字也一度成为环境保护浪潮的热门词汇,甚至引发中央领导关注批示。随后,北京市宣布投资100亿元,用5到7年时间完成对周边近千个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治理,并建设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厂。
经此一“役”,更主要的是建立在大量实地调研和影像资料的基础上,王久良对于垃圾问题的意见表达,已经显示出民间独立调查性质的权威性。
即将进入2015年的时候,王久良再度发声,用一部暌违3年的纪录片新作《塑料王国》,撕下了一个以再生资源回收、循环经济为名的产业的面纱,暴露出最为不堪的一面。
来自中国海关的官方统计,2013年,我国进口废旧塑料垃圾总量为800多万吨。王久良所记录的,正是这些垃圾在中国从南到北30多个乡镇村庄最真实的初级加工场景。
《塑料王国》第一次面向媒体的放映地点,选在北京东二环边的银河SOHO大楼。这座宣称拥有最好空气净化系统的建筑物,远远望去充满着时尚的未来感。
但是,至少在放映的这一天,银河SOHO的未来感被笼罩京城的雾霾粉碎肢解。当天,空气中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,成为《塑料王国》所要表达主题的又一个注脚。
源源不断的集装箱货车,拉着满满的垃圾进入村庄。留守农村的妇女和老人,还有那些来自更贫穷地区的打工青年,在乱糟糟的作坊里用手分拣着塑料垃圾。这些垃圾的“原产地”,多是美国、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韩国和澳大利亚。在镜头里,很多生活塑料垃圾里面掺杂着不明化学粉剂,灼伤了翻检者的双手。甚至还有一个在垃圾堆旁玩耍的孩子,拿起一个还残留着不明液体的针管,毫无戒备地直接放进嘴里玩耍。
这场景在银幕上出现时,观众发出抑制不住的惊呼。那些充斥着肮脏垃圾、浓烟、污染水的画面,那些依赖垃圾处理维系生存者的麻木与无奈,与重重笼罩都市的雾霾天气遥相呼应,让人产生一种几近环境末日的关联想象。
“我们这样落后的垃圾处理能力,为什么还要进口洋垃圾?”几乎每一位看过《塑料王国》的人,都会不解愤懑地提出这样的问题。
无疑,王久良又扔下了一颗炸弹。
巨响过后,中国乡村垃圾处理的残酷真相浮出水面。
战绩与现实
一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,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,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,从最初的7.4亿美元飙升到115.4亿美元。
疑问就此产生——中国为什么进口这么多垃圾?
王久良的回答可以概括为四个字——“利益驱动”。
“过去,一些国家的生活垃圾是需要花钱向外转移的。后来,这种垃圾慢慢有了市场,不用付钱也可以转移出去。现在,一切都颠倒了,生活垃圾竟然成为可以出售的商品。”在纪录片《塑料王国》放映前,王久良告诉记者,正是中国的进口抬高了世界垃圾的价格。
不过,王久良的观点一经曝光,便立刻招致资源再生行业相关者的强烈反对。27岁的再生资源网站编辑于泽甚至私信王久良,直接表达反对的态度。
2015年1月2日,于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断然表示:“没有人否认存在过进口洋垃圾的问题,但在绿篱行动以后,那种情况已经几乎不可能发生。”
于泽所说的绿篱行动,是国家海关总署于2013年2月启动的一次为期10个月的专项行动,旨在加强固体废物监管、严打洋垃圾走私行为。
“过去,进口的集装箱是抽检。在绿篱行动中,几乎箱箱检查,并且实行最严格的掏检。”于泽拿出一份新闻报道,上面列举了各地海关的行动成果,其中,仅在黄埔海关、烟台海关、宁波海关、黄岛海关、威海海关、青岛海关、梧州海关、佛山海关和石家庄海关,便共计查办涉案废塑料3万多吨。
“王久良的拍摄期,一定是在绿篱行动之前。”走访过很多大型正规再生资源企业的于泽,对国家的专项打击行动效果深信不疑。
“你信吗?”听完记者转述的于泽观点,王久良这样反问。“确实有段时间,拉垃圾的车少了。但有的老板直白地告诉我说,别管他们的货滞留多长时间,最后总有办法通关提走。”
事实上,究竟如何定义洋垃圾与合格废旧塑料原料,本身就界限模糊。
在于泽看来,国家的规定很明确。以废旧矿泉水瓶(PET)为例,需要在垃圾出口国完成清洗和拆解后,才能作为再生资源原料被进口到中国。
然而,现实显然并不是这样。
2011年,王久良访问美国加州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。参观结束后,美方人员不经意间指着正要开走的集装箱货车说:“你看,那是要运往你们中国的。”
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的垃圾,都是生活垃圾。经过人工初步分拣,生活塑料垃圾被分离出来。正是这些美国人不愿花钱费力处理的垃圾,被中国的商人买走。
这个不经意间的发现,让王久良产生疑问——令美国人头疼的垃圾运到中国后,到底又会如何处理?
经过1年的调研,王久良决意再拍摄一部纪录片,追踪曾经困扰自己的事实真相。
2012年5月31日,《塑料王国》正式开机。整个拍摄持续了28个月,直到2014年9月结束。
“最初3个月,几乎处于被驱赶的状态,进入不了实质性的拍摄。这样算来,大部分的拍摄素材,正好是绿篱行动期间。”王久良直言,“我不用看数据,也不用听有过什么行动,我亲眼看到并拍摄下来的,足以说明一切。”
放错位置的资源?
毫无疑问,王久良和他的《塑料王国》,似乎触动了整个再生资源行业的“奶酪”。
于泽的质疑只是开始,更多的反击接踵而至。
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周开庆先生发表的文章中,重点援引了巴塞尔公约中的观点,“塑料被认为是无毒的”,“使用塑料再生料不仅仅是成本考虑,而是发展和责任考虑”。
与此同时,一些颇具规模的正规厂家处理塑料垃圾的过程,也被用来证明《塑料王国》揭示的原始和混乱仅为个案。
对此,王久良直接反驳——在进口塑料垃圾处理的问题上,不要把利润和社会责任混为一谈。如果为的是利润,那么由此产生并在未来逐渐显现的环境污染,为什么没有让从垃圾中掠取利润者“买单”?如果是为了社会责任,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塑料垃圾进行处理,到底履行的是哪家的社会责任?
在王久良看来,一切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,都是负增值产业。如果环保型回收1吨废旧生活塑料能够产生100元经济效益,需要付出的成本,至少也要101元。否则,便无法解释在被世界公认垃圾分拣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,为什么要对企业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补贴,更解释不通为什么《塑料王国》里依然会出现日本垃圾。
事实上,一些塑料垃圾处理企业一直在吁请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。他们在例证企业深陷经营困境时的说法,客观上暴露出环境污染问题的严峻。
“塑料作为可再生资源,要回收是一定的。但是,如果没有国家足够的政策支持,企业不好做的。”从事废旧塑料回收5年的安伟(化名)说。
这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从业者,来自国内某废塑料回收集中县。两年前,这个县对散落在村子里的小作坊式废塑料分拣、造粒产业,进行了“壮士断腕,涅槃重生”式的自我革命。公开的报道中,县政府高度重视环保问题,淘汰小作坊,引导成规模企业进入工业园区,目的只有一个——建立环境友好型的再生资源回收产业。
安伟毫不讳言政府对入园企业提供了多项支持,也承认园区经营者在租金上给予了相当优惠。“就拿处理废旧塑料产生的污水来说,处理成本至少在每吨10元以上。现在,包括水费和处理费用在内,每吨污水只向企业收取6元。”但是,即便是这些已经大大压缩的污水处理成本,依然是企业不堪其重的的负担。
其实,在污水处理这个环节之外,最终无法回收的垃圾如何处置,依然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大难题。依据王久良的调查,1吨塑料垃圾的回收率,即便在运气好的时候最多也只有85%,这就意味着至少要有150公斤废弃物毫无任何用处。
对于这些纯粹的垃圾,最普遍的做法依然是填埋或者焚烧。在王久良拍摄的画面中,很多垃圾就在田间露天燃烧,黑色烟尘弥漫。
“理论上,焚烧可以用来发电,但又是一笔巨大的投资,谁投?”安伟说。
填埋呢?科学研究已经证明,垃圾填埋对土地和地下水的污染破坏,影响时间长达上百年。
无论如何,王久良和他的《塑料王国》已经搅动了一个行业。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一切判断和论断,都来自长达3年的调查。“有多少园区污水厂根本就不运行?说是统一处理,可管道都没铺通,这些我都拍到了呀。”
可惜,诸多专业人士似乎看不到这些。周开庆在自己的文章最后,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:一家企业有问题,少数人有问题,不能推而广之。随着社会对中国再生塑料产业的认知和了解,一些片面的新闻报道已经很难对行业健康发展形成多大影响。
周开庆这样说:“我们坦然处之吧。”
然而,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处之吗?
房间里的大象
行业内外的争论还在继续。
但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,王久良作品中呈现的产业最前端从业者们的纠结、贫困、损害与被损害、麻木,才是戳中人们内心痛点的元素。
“垃圾(这)东西,又不是新的,没有味?什么味都有!”画面中,一位分拣垃圾的妇女这样说。
在《塑料王国》中,围绕着通过回收废旧塑料来挣钱究竟值不值,分拣垃圾的工人们有过这样一次讨论——
“可熏得慌了,熏有什么办法。”
“其实俺也不愿意干,这东西又脏又有污染,俺自己也知道,对俺自己也不好,但是俺为了生存,没办法。”
“空气空气不好,水水不好。什么好?说句开玩笑的话,就是钱好。”
……
王久良告诉记者,片子中出镜的女分拣工干了20多年,自从有了这个产业开始就干,到现在一个月收入七八百元。而她的手,每一块关节都是变形的。另一个老太太捡到一个瓶子,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液体,只是想回收这个瓶子。结果在倒掉液体的时候,她的一个指关节全被烧焦。“瓶子里的液体是氢氟酸,一种强酸。”
王久良到田间拍摄,问当地人这些垃圾对庄稼有没有影响,回答竟是“没污染,咱实事求是”。结果镜头一转,村庄的环境变得糟糕。干涸的池塘,已经多年不见鱼虾。处理废旧塑料产生的黑色污水,直接排入河流。甚至连地下水都无法安全饮用,村民需要购买山泉水喝。“一个月十五六元吧。”老太太算计着每个月买水的费用,售卖山泉水的小贩送水的步子匆忙。
村头,一位干废旧塑料回收的老板的老父亲说着,这年头,怎么年轻人都得癌?
另一个男人,反问王久良,“你要问还有谁没得癌?”
即便如此,每个人都在维护着这个产业。
产业链上,最低端却最必要的一环上,以生存的名义忍受脏臭乃至环境被破坏的人们,对理想生活的大胆奢望,其实极其卑微。
一个年轻的小老板,最大的理想就是买辆车。终于,在一个冬天,小老板实现了这个理想,兴奋地在自己新买的二手车里坐了半晚。
“人在车里产生的热气让挡风玻璃盖了一层白雾,从一个角看进去,那老板高兴的脸,当时那感觉,真是……哎……”王久良没办法忘记这一幕,那是以生存为代价换取的梦想实现,从他的价值观看来,个中滋味,难以评说。
一家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家庭,由于贫穷,年轻的父母亲带着孩子全家打工在一家分拣作坊。家里的女孩依姐(音)早已成为分拣塑料的熟练工。她最小的妹妹,出生在这个堆满了垃圾的院落外面。11岁的依姐渴望上学,父亲却一拖再拖,理由都是“没钱”。依姐最喜欢在老板家里玩电脑,在一次争吵后,两家人关系紧张,女孩就从垃圾堆里捡出花花绿绿的纸板,在桌子上做出了电脑的模样,自己打字玩。
垃圾,就是依姐这样的孩子全部的世界。他们在垃圾里成长,从垃圾中获得玩具,甚至从垃圾中学习。而垃圾,能够给他们的,也仅此而已。
“我真的无法喜欢上他们,除了那些孩子。”王久良并不讳言自己的情绪,他与他的被拍摄者们相处时间按年计算,他理解他们的无奈、挣扎和选择,但在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让他没办法从情感上喜欢上他们。
人们知道垃圾的危害,但没人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什么。正在野外倾倒塑料垃圾的人对着镜头说,为什么不查查谁让这些洋垃圾进到中国?
这个存在于30多个乡镇的废旧塑料回收产业伴生的污染问题,似乎没人愿意来管。垃圾,像房间里的大象,切实地影响着那么多的乡村和人们的健康,而所有人选择视而不见,以生存的名义。
选择不看的,还有那些垃圾输出国。
塑料垃圾从世界各国而来,在中国获得重生,被制造成玩具或者其他产品,又重新回到美国、德国乃至全世界的生活中。没人在意,垃圾如何重生?又留下了什么。
理想主义者的坚持
2014年的最后一天,王久良踏上赴美航班。他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,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。他筹划着要在纽约、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播放《塑料王国》,让美国民众了解自己产生的垃圾,最终给大洋彼岸的中国人带来了怎样的伤害。
正是在伯克利,王久良发现了中国这个“塑料王国”。那位出现在纪录片中的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负责人丹尼尔,在看过王久良在中国拍摄的部分素材后回应说:“现在我们看到了,我认为大家应该看到这些。”
王久良意识到,美国民众关于垃圾链产业中的道德伦理选择,可能会成为影响垃圾输出行为改变的力量。
看过《塑料王国》的很多观众意识到,垃圾并不会自己消失。当中国的大门关上了,这些垃圾还会流向地球上其它国家。“你们媒体在国内使劲,我在国外使劲,大家做各自擅长的。”无论如何,王久良下定了决心,“即使是冰山,也要撬动它”。
或许,很多人都误解了王久良。
2008年,王久良发现了垃圾,从此,垃圾也黏上了他。但是,他的思考显然并不止于如何处理垃圾以及垃圾的世界战争。从始至终,他的目标是希望提出一个更为终极的命题——消费主义时代里,人究竟拥有多少算够?
几年前,记者初次采访王久良,他用着一部老式的诺基亚黑白屏手机。今年,记者再次采访王久良时,惊讶地发现,在这个全民触屏智能手机的时代,他依然固执地使用着那部落伍了好几代的手机。
王久良不过度消费,他将自己的生活需求维持在最基本的层面。与垃圾打了6年交道,电脑里全是垃圾的素材,超市里那些花花绿绿琳琅满目的包装,在他眼里条件反射式地瞬间变成它们被使用后成为垃圾的样子。
“我很想做一个展览,就叫《超级市场》,货架上摆满的不是新商品,而是摆满喝完牛奶的空盒子,吃完冰淇淋的塑料桶什么的,让垃圾填满货架。”王久良希望,人们能够从垃圾问题上,检视自己的消费,而不仅仅只是抱怨政府做得多么不够,环境如何变得糟糕。
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,所有行业都在挖空心思如何让人们从兜里掏钱出来,王久良却试图让这浮华喧闹的消费快车跑慢一点。这多少有点唐·吉诃德的意味。
小时候,妈妈带着王久良算命。“那先生说我,一生‘骑着墙头当马匹,拿着秫秸当杆枪’。”现在,相机和摄像机就是王久良的“武器”。他唯一能够仰赖的东西,与算命先生所言的“墙头”和“秫秸”无异。在这位38岁独立纪录片导演内心,始终有着最为清晰且理智的坚持。“我能改变世界的很有限,但能改变多少是多少吧。”
王久良没有想到,自己从《垃圾围城》开始,竟然与垃圾黏在一起整整7年。
围绕着垃圾的拍摄计划,并未完成。看上去,他与垃圾还要继续黏下去。